论异性恋悲观主义 #
Seresin, Asa. “On Heteropessimism.” The New Inquiry, 9 Oct. 2019, https://thenewinquiry.com/on-heteropessimism/.
作者:艾萨·塞雷辛(Asa Seresin)
翻译:amber(she/they), Claude A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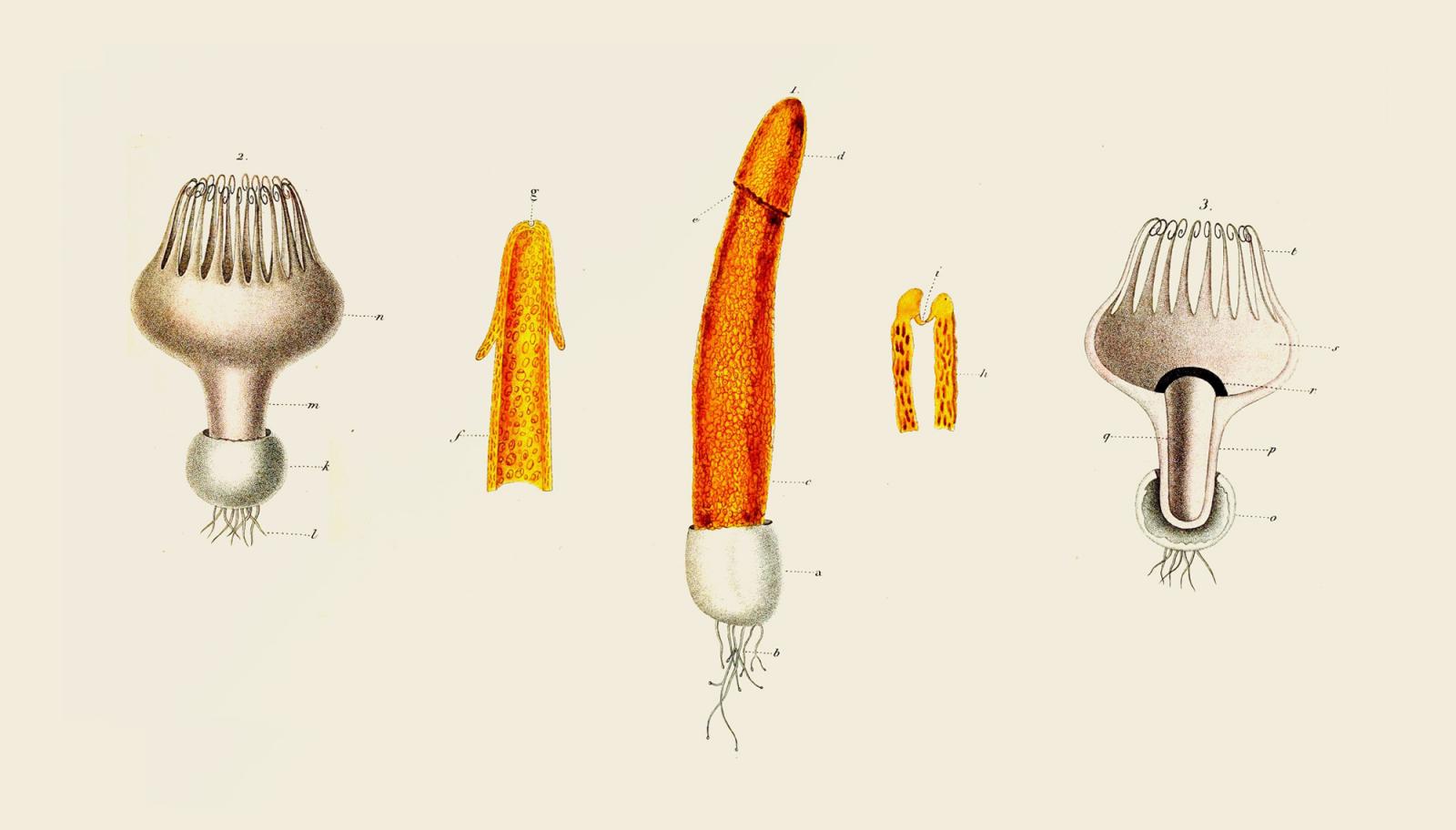
1 #
「异性恋总让我感到尴尬,」马吉·纳尔森(Maggie Nelson)在《阿耳戈船员(Argonauts)》一书中承认道。这本书曾一度在女性和酷儿群体中广受欢迎,以至于我在2016年第一次买这本书,就在一家女同性恋(dyke)酒吧里被从包里偷走了。纳尔森的这一自白,一直让我认为是我们当下时代的一个症候,在这个时代,对异性恋的指责已经成为了一种网络梗。然而,当我在一个研究生研讨班的视频会议上问及此事时,她却有所回避。她否认自己对异性恋本身感到尴尬,只是对自己的异性恋经历、对那些她曾经或正在经历对男性的浪漫吸引感到难为情。
当时,我觉得她的辩解显得多余而且不诚实。作为熟知酷儿理论的人,她理应知道,她自身的异性恋经历只有通过将异性恋与其他(不那么尴尬?)的亲密关系区分开来才能被审视。无法将自身的直人经历与异性恋这一制度区分开来——如果你对前者感到尴尬,那么对后者也必然如此。异性恋从来都不是个人的问题。
我现在看到,纳尔森的辩解实际上是异性恋悲观主义的典型表现,这种情绪模式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当下尤为明显。异性恋悲观主义包括展演性(performative)地与异性恋划清界限,通常表现为对异性恋经历的遗憾、尴尬或绝望。异性恋悲观主义往往把男性作为问题根源。这种划分界限的「展演性」并不意味着它们不真诚,而是它们往往并不伴随着真正对异性恋的抛弃。 当然,有一些异性恋悲观主义者会根据自己的信念采取行动,如独身或已经过时的政治女同性恋主义(political lesbianism)选择,但大多数人依然坚持异性恋生活方式,尽管他们认为异性恋是无可救药的。就连自暴自弃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也强调自己的处境是非自愿的。
社交媒体是展演性的去认同化天堂,异性恋悲观主义在这里肆虐。最近在网上引发一股异性恋悲观主义浪潮的,是波士顿直人骄傲(Straight Pride)事件(就像右翼网络的许多事物一样,这个事件本身并不重要,但含义深远险恶)。波士顿市政府同意该活动获得许可的同时,他们又拒绝了该活动方使用一面新设计的「直人骄傲旗」的请求——正如社交媒体用户们争先恐后地指出的那样,这面旗帜令人遗憾地类似于黑白相间的囚服。
「异性恋是一座监狱!」有人高喊道,言辞呼应了异性恋悲观主义的一个核心信条。许多人借机嘲笑直人骄傲活动及其相称的暗淡旗帜,不出所料,其中大多是酷儿群体,但加入了嘲讽行列的也不乏异性恋者。在推特上简单搜索「异性恋是座监狱」这个短语,你会发现这句话既出现在对异性恋体验的内部抱怨中,也出现在酷儿群体为自己生而为同感到庆幸的人的言论中。
面对直人骄傲活动,许多人热衷于强调自己并非那种异性恋者,事实上,他们对于自身的异性恋感到羞愧。说到底,他们觉得自己被囚禁在异性恋的监狱中是违背自己意愿的。(监狱这个比喻可能被视为废除主义开始获得主流认同的令人鼓舞信号,也可能被视为人们仍然过于随意地将监狱化加诸于他人的一个令人不安的提醒。)他们摒弃异性恋的做法,很像白人对「白人爱做的事」开起了玩笑,两者之间的相似之处在于,直人骄傲活动与白人至上主义运动之间存在着不祥的亲缘关系。然而,尽管借助展演性的距离化机制来为自己在白人身份或异性恋身份上开脱,看似很「进步」,但现实往往不过如此。如果异性恋悲观主义的目的是个人的赦免,那它就无法带来正义。
2 #
展演性地与异性恋划清界限,对女性来说很有吸引力,其中原因由异性恋悲观主义的一个模因化前身总结:过度黏人的女朋友。这个早期的网络梗描绘的并非实际行为,而是一种滑稽可笑的男性噩梦,一种令自由自在的男性难以自我定义的,病态痴缠的伴侣形象。有趣的是,这个梗最初源于一段模仿贾斯汀·比伯2012年热门单曲《男朋友(Boyfriend)》的视频,视频开篇就响起了这句现已驰名的浪漫威胁:「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我永远不会放开你。」在异性恋文化中,这种过度占有嫉妒这样的负面特质——在现实中,这是导致男性对女性实施家庭暴力的最常见诱因之一——被重新包装并贩卖为女性的特征。如果过度黏人的女朋友梗体现了男性的异性恋悲观情绪,那么女性的反应则是极力表现出自己完全没有依恋——对男性和异性恋总体上都没有依恋。随后, 大量 展示 这种 不依恋 状态 的网络梗应运而生,很快就成为女性表达异性恋悲观主义的一种基本模式。
在这个意义上,异性恋悲观主义是李·埃德尔曼(Lee Edelman)所说的「麻木感觉(anesthetic feeling)」:「一种旨在防止对过于强烈情感的感知,以及一种可以在疏离中存在的依恋。」异性恋悲观主义的麻木效应特别诱人,因为它能将女性和那些被异性恋文化视为耻辱的特质——如过度依恋和「对过于强烈情感的感知」——进行分离。许多异性恋悲观主义情绪以幽默的形式表达,这与亨利·伯格森认为喜剧能带来「短暂的心灵麻木」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与传统喜剧不同,异性恋悲观主义是反自我放纵的。它的结构是预防性的,旨在提前进行心灵麻醉,以规避异性恋文化的普遍糟糕状况以及日常浪漫痛苦的剧烈下降。例如,在围绕布雷特·卡瓦诺(Brett Kavanaugh)听证会的媒体风暴中,喜剧演员所罗门·乔治奥在 推特上写道(获得超过 23,000 次转发和 142,000 个赞):「今天是一个提醒,如果同性恋是一种选择,那么在今天之后,可能会只剩下两三个异性恋女性。」这句话开头和结尾使用了同一个词,暴露了异性恋悲观主义中普遍性和特殊性的混淆。卡瓦诺是对一个预先存在事实的「提醒」——即,没有女人会选择做异性恋,但这一事实却也以某种方式由「今天」、由现在这种特殊的糟糕状况所产生。
3 #
和大多数网络亚文化一样,异性恋悲观主义与市场也存在着矛盾关系。它常常被构框为一种反资本主义立场,可以被理解为拒绝资本主义曾经要求的「美好生活」,即婚姻消费和财产所有权。然而,这种美好生活从来就与边缘群体无缘,如今几乎所有人都难以企及。如果说过去的消费主体是夫妻二人,那么如今这一格局已经崩塌,或者更准确地说,已经被新的二元体取代了,即个人消费者和她的手机。毫无疑问,大型约会应用程序的目标就是让人们保持单身。Tinder 在其有史以来的首个品牌活动中就已经明确表达了这一点,广告中有一位神气活现、看似无忧无虑的白人美女,配字是「单身可以为所欲为」。保持单身,保持渴望,让你的欲望数据像金子一层层累积起来。
异性恋悲观主义助推了这一个体化进程,不仅是因为它抽去了异性情侣形式的吸引力,更重要的是,尽管异性恋悲观主义被宣扬为一种普遍情绪,但它似乎总是在个人层面运作。集体改变异性文化的条件并非异性恋悲观主义所关注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便异性恋悲观主义以病毒式广为传播,它实际上强化了异性恋的私有化功能。 在异性恋悲观主义的视角下,女性可能不会将自己视为在这场残酷的约会「市场」中相互竞争,但将异性恋视为个人问题就切断了团结一致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MeToo 或南非反对亲密伴侣暴力的 #MenAreTrash(男人都是垃圾)运动,都展现了异性恋文化迫切需要彻底革新的可怖紧迫性。异性恋悲观主义看似可以作为这场革命的起点,但实际上,其麻痹力反而在某种程度上遏制了这些运动的动力。 如果「异性恋」成为厌女主义的代名词,恰当的批评对象就会遭到忽视。对异性恋永久性、预防性的失望等于拒绝改善异性文化的可能性。 当然,这与常常针对「非洲悲观主义(Afro-pessimism)」(将反黑主义 antiblackness 视为跨历史地结构世界存在的力量的思想流派)的批评如出一辙。非洲悲观主义和异性恋悲观主义都是对所谓「不可改变状况」的反应,但除此之外,它们的共鸣大多只存在于形式层面。异性恋悲观主义中的「悲观」比非洲悲观主义更加字面、更加基础(从字面和本质两个层面理解)。部分因为这个原因,异性恋悲观主义更加明显地阻碍了社会变革。
与非洲悲观主义者不同,异性恋悲观主义者对他们认定为「无可救药」的事物负有责任,无论他们多么希望通过否认来逃避这种责任。某些异性恋悲观主义路线,将异性恋失灵的全部责任归咎于男性,因此成为年轻女性(尤其是白人女性)学会否认自身残酷和权力的无数方式之一。 就像大多数女同性恋者一样,我曾无数次遭到酩酊大醉的异性恋女性哀叹自己的取向,坚称「做同性恋会容易得多」。当然,也许她们说得有道理!然而,「男人都是垃圾」并非我个人愿意投入争论的问题。但当一个人宣布她希望成为同性恋时,她却疏忽掉了自己实际上选择了依然依恋异性恋——成为那些(比两三个略多一些)尽管遭遇一切,依然坚持异性恋的女性之一。
4 #
女性并非唯一的异性恋悲观主义者。从愤怒的「非自愿独身者」(incel)到抱怨自己「老婆老枷锁(old ball and chain)」的已婚男性,男性同样受到异性恋悲观主义的影响,尽管和其他感受一样,他们并不被鼓励表达出来。需要说明的是,男性的异性恋悲观主义主张往往在伦理和逻辑上都与女性不同。相反,它们是对女权主义抱怨的一种扭曲反映。 在脸书(Facebook)上,这种曲解最为明显,男权主义者的努力使管理员将「男人都是垃圾」划分为仇恨言论,并暂停使用这一语句的账户。(而用户可以无视惩罚地发布「女人都是垃圾」。)
异性恋悲观主义已成为男性用来将性别平等诉求和日常浪漫伤害均解读为全球女性阴谋的证据的框架。最著名的男性异性恋悲观主义网络梗声称,#MeToo 运动使约会变得对男性太危险了。最狂热的男性异性恋悲观主义者,由于真正选择了付诸行动而受到其他男权主义团体的嘲笑,他们聚集在「男人自行之路(MGTOW)」的可喜旗帜下。MGTOW 坚持认为,女性狡猾、寄生且本质上是邪恶的,异性恋完全有利于女性而对男性极度危险,唯一的解决方案是男性远离婚姻、生育,甚至根据某些人的观点,远离约会、性行为和手淫。
其结果是对女权主义的一种奇怪嘲弄。与异性恋关系不同,MGTOW 鼓励男性形成同性照料社区,既能保护他们免受浪漫创伤,又能治愈他们的伤痛,确保一种持久的心灵麻木。 该运动严重依赖互联网,使其在现实中的影响力难以衡量。其成员大量制作网络梗,在线论坛是他们选择的自我意识提升场所。然而,即便 MGTOW 在现实中成为一股重要力量,他们选择自我隔离的做法,实际上使他们成为了最不具威胁性的男性异性恋悲观主义者。更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认为当代文化剥夺了他们「拥有女性」的「权利」的人,他们选择了基于这种信念采取行动。
5 #
在2019年杜克大学女性主义理论研讨会上,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将异性恋悲观主义认定为当代社会权力剧变的产物:「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当特权解体时,它会大声疾呼,人们失去了相互共处的信心,无法解读彼此,甚至连自己的欲望都无法把握……就像、脑残男以及许多新兴的反性女权主义者所体现的那样。」到目前为止,这是我发现的唯一一次,对女权主义和反女权主义两种异性恋悲观主义传统之间存在联系的明确承认。
这种理论上的空白并不令人惊讶。异性恋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对象,在性研究领域刚刚兴起时,它就被更性感、更酷的酷儿理论项目挤到了一边。酷儿理论家傲慢地将异性恋当作被他们抛在身后的东西。这样一来,他们反而将自身固定在了异性恋仍被普遍视为一种理想的生活方式的时期。在简·沃德尖锐的著作《非基:直男之间的性(Not Gay: Sex Between Straight White Men)》中,这位社会学家选择不是根据追求的性行为、而是根据「他们享受异性恋文化」[来定义直人]。简单地说,性态(sexuality)『正常』适合他们。这种感觉很好;就像在家一样。」这种对异性恋认同的单一描述,完全无视异性恋悲观主义的可能性,与我们当下的现实相去甚远。
与即将到来的酷儿世界令人兴奋的可能性相比,异性恋显得单调乏味而且可预见(就像斯凯普塔(Skepta)在最近一首 异性恋悲观主义歌曲中所说的「老一套」)。事实上,就在异性恋的女性主义理论化几乎彻底破产的那一刻之前,朱迪斯·巴特勒在写作《性别麻烦》之前写道:「正因为它注定要失败,但仍在努力取得成功,异性恋认同的项目因此陷入了无尽的重复。」
在原地打转、无休止地重复、毫无进展——异性恋悲观主义者和酷儿理论家都确信,这就是异性恋永恒的命运。我认为他们是错的,有证据表明异性恋文化正在发生变化。但即使不是这样,我们也必须相信它是可以改变的,因为目前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妇女 因此而死,被自己的丈夫、男朋友或前任谋杀。(几乎所有的恐怖分子都有 家庭暴力历史,这显然表明异性恋对于任何性别的人,只要他们碰巧身处电影院、学校、办公室或购物中心,都构成致命威胁。)是的,普遍酷儿化和取消性别也许是我们最终前进的方向,但在此期间会发生什么呢?
对于女性来说,彻底改造异性恋可能要从坦诚描述异性恋到底有哪些诱人之处开始——房子明显已经着火了,但是里面是否还有值得拯救的东西?异性恋悲观主义完全禁止了这种描述,因此必须从超越异性恋悲观主义主义视角的对话和叙事中汲取养分,哪怕只是暂时如此。
我们可以在作家哈伦·沃克(Harron Walker’s)的播客《为什么我喜欢男人》中找到这样一段对话。在第一集中,嘉宾拉里萨·法姆(Larissa Pham)呼应了嘲笑直人骄傲的人们:「异性恋是一座监狱……异性恋真糟糕。」法姆将异性恋视为一种叛逆、痛苦主义的欲望;她告诉沃克,她之所以喜欢男人「是因为你不知道什么对自己是好的……然后你便会被那些会毁掉你的东西所吸引。」后来,法姆重申了那种熟悉的含义,即没有女人会主动选择异性恋:「我认为你无法选择被什么吸引。」
然而,在整个对话过程中,法姆也列出了一些她觉得男性有吸引力的原因,比如「粗壮的手臂」「阴茎」和「男性的气味……大多数男人的气味」。在随后的几集里,其他嘉宾也提出了自己对男性魅力的看法。塞达·哈默尔(Theda Hammel)认为,女性之所以被男性吸引,是因为与男性亲密接触会让自己受到肯定:「一个女人喜欢男人——或者一个跨性别女性特别喜欢男人——并不一定是因为男人很有吸引力……只是因为作为与你不同的存在,他们让你喜欢自己内在的品质外露了。」尽管这些观察看似明显,但很少被人明确说出。听到它们如此坦率地说出,就暴露了异性恋悲观主义主义是如何压制女性欲望表达的。
《为什么我喜欢男人》半开玩笑地问出这个问题——你可以听到沃克在每一集开始时说出这个问题时语气中的那份狡黠笑意——但它同时也是一种诚恳的探究。沃克通过反复提出这个播客的同名问题,突破了异性恋悲观主义主义造成的麻木感,重新唤醒了自己的脆弱。从这个角度看,异性恋并非一种不可救药的诊断,而是一个可能的实验和变革场所。
长期以来,异性恋的常态化使其可以被无休止地重复,免受任何实质性改变。如今,异性恋悲观主义,实际上可能模糊了异性恋正在发生变化的程度——即便它也在引发这种变化。 没有一个不可篡改的批评对象,异性恋悲观主义主义的逻辑就会崩溃。非常反常的是,这造就了人们对异性恋持续性的新投入,重新铭刻了异性恋疲惫的特征,即便这种投入采取了负面情感的伪装形式。从这个角度看,异性恋悲观主义,揭示了我们如何能够暗自依恋于那些我们(诚恳地)斥之为有毒、无聊、崩溃的事物的延续性。 面对失望的可能性,麻木感就像一剂止疼药。